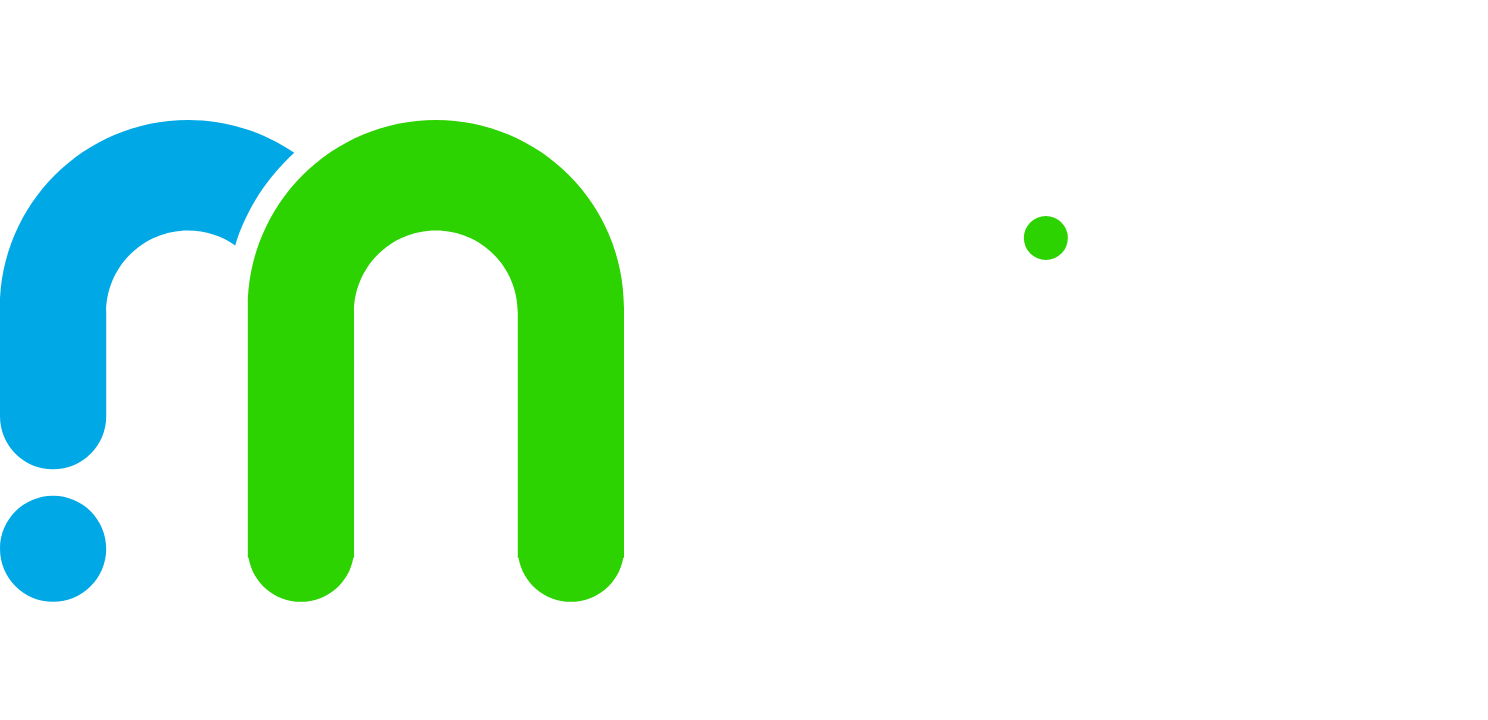爸爸开始驯鹰了,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了解了这件事的残酷。两结实的牛皮条,像脚镣一样卷在双脚上,皮条末端都接在一个杯口大的铁环上。爸爸给鹰戴上一个特制的皮面罩,使鹰只露出口鼻,然后把鹰架在有皮套袖保护的胳膊上,另一只手死死地握住铁环……鹰嗷嗷地低吟着,似乎在叫:“天呢?青天何在?还我的天!还我自由……”虽不知天 在何处,它依然要冲。只要它一飞,爸爸就用力向下拉那个铁环,把它强拉回郅胳膊上。一飞,一拉;再飞,再拉……这是一场人同禽兽的较量……鹰终于不再飞了。它张葑嘴“呼呼” 地喘着气,两腿打颤,就是想飞也没有力气了。爸爸松了一口气,抬起拿铁环的手抹了一把汗,笑着说:“第一步算到家啦。”说罢给鹰解去了面罩,它仍然很老实,没有要飞的表现。可我却在它那冷漠的双目中看到了一丝怨恨,我的心不禁颤了一下。
鹰被拉过后,往日雄姿一去不退,无精打采,呆若木鸡。 每天只是透过窗户呆呆瞪视着蓝天,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我知道,它是在怀念那任它飞扬跋扈的天空,它是在追忆那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,它那饱含着原始野性的血液并未因爸爸的折磨而屈服。我的心越来越沉重,我试着劝爸爸不要培养仇恨,把鹰放掉吧。可他把眼一瞪,说我心太软,成不了男子汉,还扬起手吓唬我说要是给他捣乱饶不了我。可每当我的眼睛接触到那冷漠的鹰眼时,心里就是一抖,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。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啊。 一个声音在我内心深处喊,而且越来越大:“还它自由!”
机会终于来了。爸爸一早就去买建鹰房的木料了,家中只有我和鹰。可能由于令它恐惧的“人走了,鹰有些活跃了,它在栖木上走來走去,喉中低吟,不时抬起头偷偷看一眼天。忽然猛一弓身子,展翅向窗外扎去。可由于皮条的缘故,它刚飞离栖木二尺来高就被狠狠地拉住了,可它依然昂着头,费力地拍打着双翅,奋力想向空中飞去。我想,山野对它的召唤,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。栖木在它那大力拉扯下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求救声。看到这儿,爸爸那扬起的手在我眼前消失了。 我冲过去猛地推开窗子,又剪断了鹰脚上的皮条。鹰掉在了地上,可它马上一翻身,抖擞一下翅膀,箭一般毫无留恋地飞向那早已向往的天空……我的心放下了。
从那以后,每当我想起它,都感到无比的髙兴和欣慰。我能不高兴吗?我把自由还给了一只向往山野的鸟,而自由是任何人,任何鸟兽都想得到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