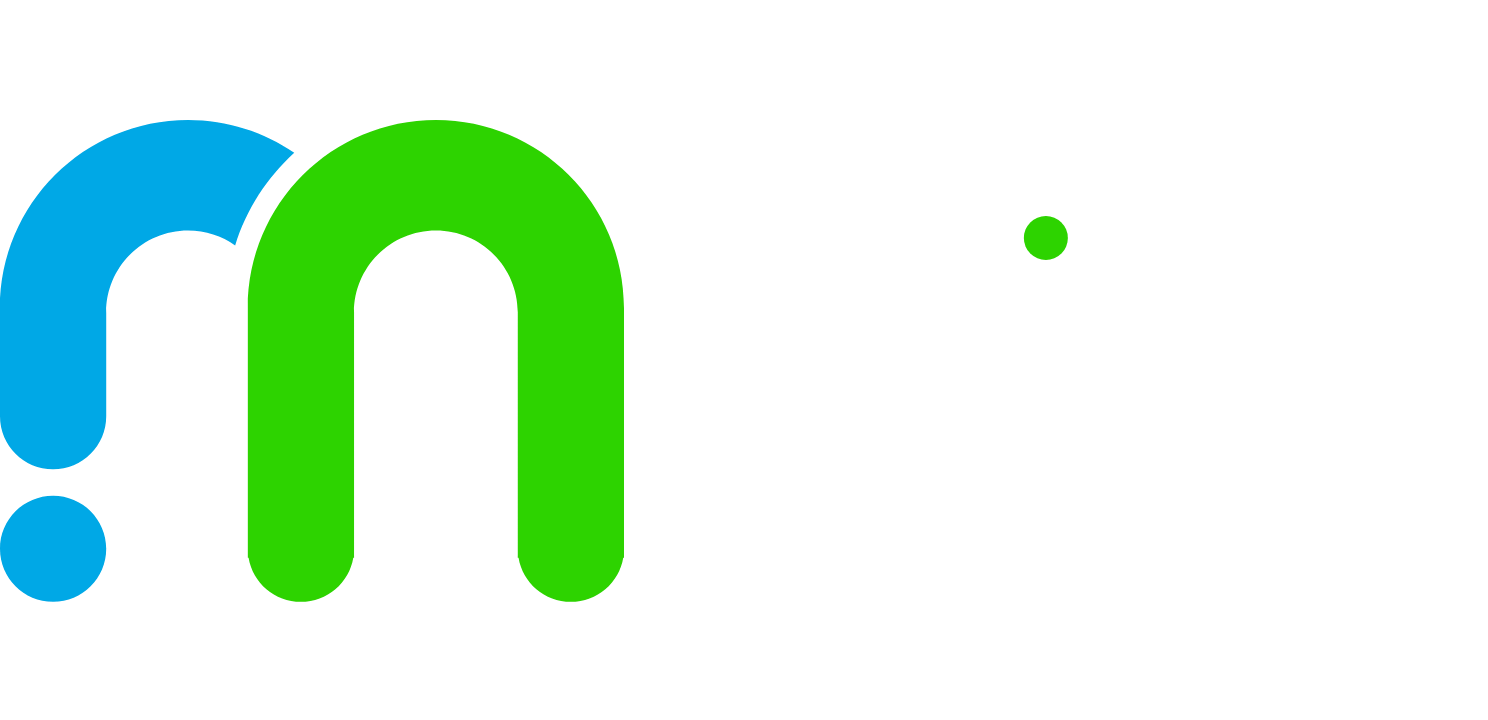除夕晚上,儿子、孙子都来到她身边,她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,就像盛开的菊花瓣,每根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
吉老秤已经五十几岁,可是身体硬实得像一座石碑;从口外刚赶来的儿马蛋子,一噘子踢到他的胸脯上,就像被跳蚤弹了一下。他的手艺高超,远近驰名,却只能混个半饥不饱;用他的话说,一辈子没吃撑着过。他脾气暴,不娶家小,不信鬼神,只好喝烈酒闻鼻烟;喝醉了就睡觉,扯起鼾声像打雷,打起喷嚏像放炮。
老汉一面听着,一面捋着像干老玉米须一样的胡子。
老人的那个驼背向上拱起,就像一座小山一样。
老人的手每一根指头都伸不直,里外都是茧皮,整个看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。
老人的手指瘦得像螃蟹腿。
老人头发乱蓬蓬的,拖把布似的长发像是好多个月没有梳理了。
老头儿瘦骨嶙峋的胸脯犹如一条一条的百叶窗。
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,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。可是那晒得干黑的脸,短短的花白胡子却特别精神,那一对深陷的眼睛特别明亮。很少见到这样尖利明亮的眼睛,除非是在白洋淀上。
那老汉两条哆里哆嗦的弯腿几乎站不稳,像弱不禁风的干树枝。
奶满脸爬着重重的皱纹,因为带有笑容,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。
十字路边有一个老妇人,略微有些驼背,胖胖的身躯,费力地打着伞在空旷的路上艰难地行走。狂风夹着大雨扑面而来,她使劲向前躬着身子,抓紧伞,进一步,退半步,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。
我的奶奶今天的穿戴与平时大不相同:头戴绒线帽,身穿一件崭新的黑呢子大衣和一条混纺呢裤子,脚上穿着一双油亮亮的平底皮鞋。她手拄拐杖,满脸洋溢着喜气,手里拿着一张的红纸出了门。
爷爷退休已有两年了,瘦瘦巴巴的身架,一脸的鱼网纹。头顶上灰白的头发,好像戴着一顶小毡帽。笑起来下巴颏高高地翘起,因为嘴里没有几颗牙了,嘴唇深深地瘪了进去。
爷爷长着一副古铜色的脸孔,一双铜铃般的眼睛,尖尖的下巴上,飘着一缕山羊胡须。他高高的个儿,宽宽的肩,别看他已年过古稀,可说起话来,声音像洪钟一样雄浑有力;走起路来“蹬、蹬、蹬”他,连小伙子也追不上呢。
一位神采奕奕的胖老头听见狗叫,从屋里出来。他年纪六十上下,一头浅褐色的头发保养得很好,只是胡子已经花白。这就是勃洛耶尔教授。
由于多年的操劳,爷爷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松树皮,裂开了一道道口子,手心上磨出了几个厚厚的老茧;流水般的岁月无情地在他那绛紫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,他那原来是乌黑乌黑的头发和山羊胡子也变成了灰白色,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是那么有神,尽管眼角布满了密密的鱼尾纹……我想念爷爷。
这老汉,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,露在帽沿外边的头发已经斑白了。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、黄不黄的褂子。整个脊背,又黑又亮,闪闪发光,好像涂上了一层油。下面的裤腿卷过膝盖,毛茸茸的小腿上,布满大大小小无数个筋疙瘩,被一条条高高鼓起的血管串连着。脚上没有穿鞋,脚板上的老皮怕有一指厚,……腰上插着旱烟袋,烟荷包搭拉在屁股上,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。
这位老汉的眉毛胡子都花白了。但脸膛仍是紫红色的,显得神采奕奕。他身穿崭新的青布棉袄棉裤,头上还包着一块雪白的毛巾。老汉蹲在地上,乐滋滋地抽着旱烟。
由于多年的操劳,爷爷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松树皮,裂开了一道道口子,手心上磨出了几个厚厚的老茧;流水般的岁月无情地在他那绛紫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,他那原来是乌黑乌黑的头发和山羊胡子也变成了灰白色,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是那么有神,尽管眼角布满了密密的鱼尾纹……我想念爷爷。
老人清瘦而憔悴,脖子后面满是深深的皱纹。老人的脸颊上布着棕色的斑点,那是良性的皮肤病,是常年在热带海面上,太阳反射造成的结果。那些斑点沿着双颊往下蔓延,手上是深深的疤痕,那是用绳索捕获大鱼的印记。但是,这些疤痕都是以前留下来的。它们就像无鱼的沙漠上的水土侵蚀的痕迹那般古老。
老人全身上下无不呈现老态,除了他那双眼睛,如海水一般的幽蓝,炯炯有神,透着一种永不服输的气质。
男孩从床上拿起那条军用毯子,搭在椅背上,盖住了男人的双肩。那是双奇怪的臂膀,虽然苍老,但是仍然有力。当老人睡着的时候,他的头部往前面耷拉着,脖子后背的皱纹拉平了,脖子看上去也是那么有力。他的衬衫上满是补丁,就像那一面帆,而且太阳将它晒成了深浅不一的颜色。老人的头已是白发苍苍,闭上眼睛的时候,脸上没有一丝生气。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,老人的手臂压在其上,这样才没有被晚风吹走。他打着赤脚。
爷爷与泥土打了40多年的交道,他赶着牛,在田里来来回回走了大半辈子,犁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田沟,也在爷爷的额头上犁下了那深深的皱纹,那几亩田里洒下了爷爷的滴滴汗水。
他一脸慈爱沧桑,年轻时乌黑的头发已有如严冬初雪落地,像秋日的第一道霜。根根银发,半遮半掩,若隐若现。脸上条条皱文,好像一波三折的往事。